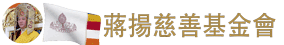| 仁波切與青年志工對談 |
|
時間:7月6日 仁波切致詞 在多年培育志工的過程中,我個人有一些探討。絕大部分都是好的,大家都很熱情,而且知道志工就是行善的開始,這是值得肯定的。可是島內慈善團體的發展,有所謂「太陽、星星、月亮」的趨勢。太陽一出來,月亮不見了,星星也被掩沒了,但是他們全部存在啊! 提到行善、捐錢、做志工,有人坐火車三小時,當志工一小時,回來又再搭車三小時,他們覺得很滿意,因為在那一小時得到了無上的榮耀。這樣不能說不對,但是就時間成本而言,在台南、我們的家鄉,也有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基金會、慈善團體在做同樣的事情。今天諸位願意來到這裡,我感到很高興。 志工是一份高尚的付出,不求回報,而且是在自己的自由意願之下,歡喜來做,歡喜承受。有人說:「歡喜做,甘願受」,我覺得這樣子還不夠積極,應該是「種什麼因,得什麼果」,所以「歡喜做,就會歡喜受」。 認知決定未來,你的態度會令自己成熟,用對的態度,就會讓自己的思慮更加成熟。 「偏遠山區學子美夢成真」是蔣揚長期推動的一項服務。有一戶是家徒四壁的,真的是一間房屋,裡面什麼都沒有,讓人看了很心酸!當初我們發現這戶個案時,他們家裡沒有日光燈,因此買了檯燈給孩子。第二個月去訪視時,孩子沒有用檯燈,家裡明明有電、有插座,也不是不會用,孩子說:「我爸爸沒有錢繳電費,所以沒有用。」對於這樣的孩子,要怎麼說?只有不捨啊!電費一個月才一、兩百塊,但是他節省,於是蔣揚發補助金給他。」 現在的年輕人、覺得不滿意現狀的人,應該多出來接觸這些邊緣地區的弱勢孩子。可能你用過不要的,或是你不再喜歡的東西,對他們來說都是寶貝。 青年志工:昨天我們這一組去拜訪四位老人個案。跟他們談話、接觸時,有時會想到自己的親人。跟老人家不是很快就可以聊上話題,但因為老人不方便,就想幫忙他,可是他們要自己來,婉拒我們的幫助。面對這種情形,一開始我覺得蠻挫折的,可是想一想,既然他們可以自己做,我們在旁邊看著、輔助他們,應該也就可以了。等到他們真的需要幫忙,相信他們會開口。 仁波切:對,你點出了幾個問題。第一,老人家婉拒你的協助。為什麼老人家婉拒你?我想,任何一個人,只要自己還動得了手,通常都不願意假他人之手。 青年志工:仁波切你好,我們去訪視兩戶。第一戶的爸爸在,妹妹也在。到另一戶的時候,發現家裡沒有長輩,只有三個兄妹,哥哥在外面看看空地,妹妹在玩電腦。趁他們填資料時,我們藉機跟他們互動、聊天,調侃自己長得不高,自己很矮之類,最後玩遊戲,透過遊戲增加彼此的熟悉度。我們玩開之後,老師說從來沒在他們臉上看到那樣的笑容,他們真的很快樂!之後我們一起喝飲料,一起坐在馬路上聊天,看著雲從很亮變暗,看著電線桿上的蘭花,還有小溪流,覺得還蠻不錯。 仁波切:你長大了,真的。前兩年他還很叛逆,跟他講東,偏要往西,剛剛這一席話讓我很感動。從別人的借鏡,可以看到自己的過去,這是具有觀察力和反省力的特質。一個人如果沒有觀察力、沒有反省力,將看不到自己的內心。 青年志工:你好,我去訪視「八家將」,一戶有八個孩子。他們現在的生活還蠻不錯,電視比我家的還大,電腦好像也比我家的還好。我不知道他們過去是怎樣,去看時覺得環境還不錯,有那麼潦倒嗎? 仁波切:我們被訓練成眼見為憑,眼睛看到才要相信,可是眼睛所見不一定是真的。以「八家將」這戶個案來說,如果不了解他們的過去,便容易誤解。你所看到的電視機、電腦,都是後來有善心人士捐給他們的。 青年志工:也有她對的地方吧!送去安養院會不放心,而且要錢。 仁波切:可能要一些錢,但可以申請補助。 青年志工:如果送去安養院的話,外界就不知道她家的狀況,沒辦法繼續獲得外界的支援。 青年志工:那個媽媽寧願接受外界的援助,也不去工作。其實外面應該還有很多比她更需要的人。 青年志工:站在他們私人的角度來講,一來,在醫院可以受到比較好的照顧,最好是妻子和三個兒女都在他的旁邊,這樣植物人才有機會復甦起來;二來,他們得到的資源也比較豐富,這種做法雖然比較自私,可是誰不自私呢? 仁波切:這是新人類的看法,不能說不對,但忽略了一點:長期下來,真的可以獲得社會資源嗎? 青年志工:當然不是長期的,這可能是一個比較過渡性的方法,前提是植物人能夠復甦起來。 仁波切:站在社會服務、慈善事業的立場,我們比較主張急難的、短期的救助,如果要長期,真的是沒有那樣的社會資源。我有許多弟子擔任醫生,有人在加護病房工作,當急診室的主任。他非常非常苦惱,來找我談了三次。他說,站在醫生、家屬的立場,都希望把病患救活。許多病人年紀大了,但家屬就是不願意放棄維生系統,堅持一定不可以拔管,因而許多比較年輕的病人就沒有機會,因為一個加護病房只有幾套維生系統而已。外面送來車禍的年輕人,沒有維生系統可用,就往生了。他問我要怎麼辦? 青年志工:假設病人拔管只是暫時的不適應,但還活得下去,還能維持生命跡象,那就先給年輕人用。 仁波切:誰可以決定拔管之後,病人可以活下去?他如果可以活下去,早就要拔管。 青年志工:就社會道德來說,應該是先到先用。如果從宗教的看法,眾生平等,人人都有機會用。我可能會採取比較客難的方式,看能不能用人工的方式把生命維持下來。 仁波切:沒有那麼多人工資源可以用。問題的關鍵在於,維生系統長期被占用。 青年志工:救外面那個。 仁波切:可是裡面那個怎麼辦? 青年志工:因為他老了。 仁波切:如果被人聽到,你會被罵。 青年學生:適者生存。 仁波切:這樣家屬會告你。我同意你的觀點,問題是方法,要如何讓裡面長期佔有維生系統的家屬可以接受? 青年志工:想辦法跟他們溝通。 仁波切:就是溝通不了。 青年志工:轉到別的醫院。 仁波切:別的醫院不收。 青年志工:看他們要不要先轉到一般病房? 仁波切:一般病房沒有維生系統,他們需要那個維生系統。 青年志工:再訂做一個。 仁波切:那一套幾百萬,家屬也不可能花那個錢。你們想不想知道我的答案? 青年志工:想。 仁波切:想辦法圓滿。因為他已經腦死,活著只是一種假象。我不知道後來這位醫生有沒有這樣圓滿照做,但他事後告訴我,他救了很多人。 青年志工:我去訪視山區瑞豐國小附近的三兄弟,坐了很久的車,都是山路。昨天只有二弟和三弟在家,老大跟爸爸出去工作。山區的資源真的非常缺乏,每戶之間可能根本不認識,距離好幾公里。經濟資源雖然很重要,可是他們比較需要我們去做溝通。像二弟是升國中,有一些感情的事,不想跟爸爸媽媽講。或者有些是跟爺爺奶奶住,但無法跟他們分享,就需要我們去,可能年齡層比較接近。 仁波切:恭喜你,上了我們台南縣最高學府。那個國小的海拔是台南縣最高,所以說是台南縣最高學府,但人數最少。每個學生從家裡到學校,走路大約要一個小時以上,所以平常上課時就住校。有的小孩要自己洗衣服,我們捐助過洗衣機。 |
|
相關連結: |